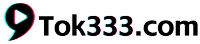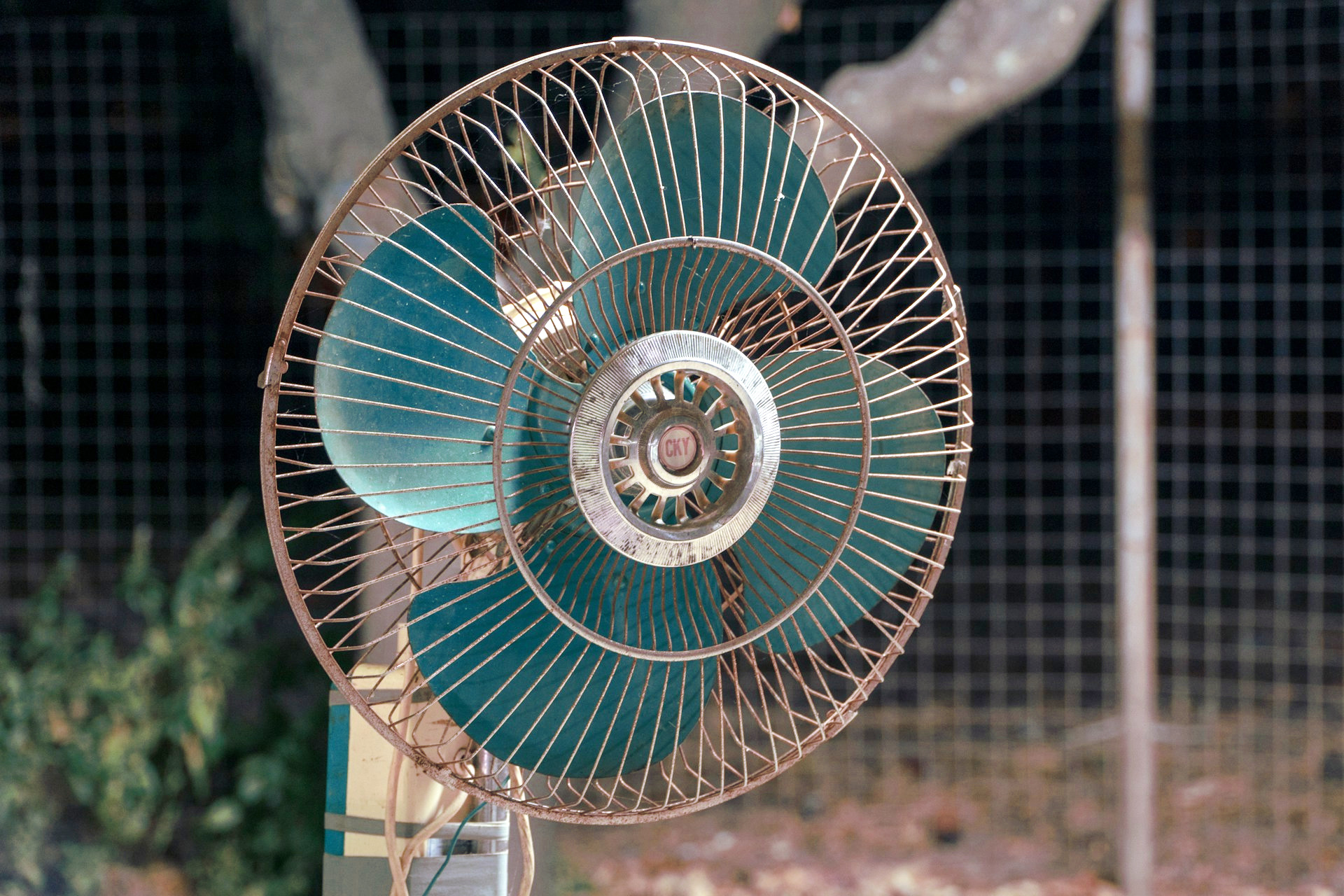责任编辑: stdph.com
拿破仑时代的美食作家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 Savarin)说的那句:“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村上春树的那句“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一样,属于味觉生理学的至理名言。
我还记得看某部美食纪录片,一位女嘉宾谈起家乡的云南过桥米线,大概意思就是即便在北京吃到的米线都很正宗,但是在米线的烹饪制作过程中的空气、湿度、温度或者气候状态,始终都还不是如家乡那般原汁原味。看到这里,我觉得我应该更明白三个世纪之前的法国美食作家为什么可以一针见血地写明人们对于食物的依恋以及对于一种风物的向往。不仅云南的米线是这样,我想在上海的新疆菜也是这样。
每个人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地域色彩的菜肴的热爱,来自于他们过往的生活以及成长的经历。而在那些相对于没有养成和他们一样饮食习惯的局外人看来,很多时候菜肴的吸引力是来自于一种反传统的刺激,即便是这些菜肴已经成为了主流。
但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也许正是因为永不满足的胃口造就了对于这些异族他乡的菜肴的追求,而那些对餐桌上的食物充满了热情的人们,他们的成长经历以及各种关于食物的回忆,也成就了很多关于美食的传奇故事。这就是人们经常可以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吃饭的原因,虽然我并不能从各种兼容并蓄的饮食中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是我应该很清楚一顿晚饭还是可以透露很多有意思的话题。
二爷是上海一家意大利餐厅的股东,同时也是比利时著名漫画作品《丁丁历险记》在国内展览的发起人。他过去二十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宜山路的维吾尔餐厅吃烤串和拉条子。他对于新疆美食的热爱甚至超过了他自己投资的意大利餐厅的美食。而小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从新疆来上海求学,后来工作生活在上海,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寻找上海新开的新疆餐厅,然后用他少年时期建立的味觉体系去评判他去的新疆餐厅是不是很正宗。
上海的马里亚女士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她维吾尔族的丈夫在上海相识相爱,两人结婚之后便开了这家维吾尔餐厅。我跟二爷一起去她的餐厅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她用上海人的味道将她餐厅的菜式做了很多的改良。一家可以在上海经营近三十年的新疆维吾尔餐厅,应该也是上海的一个海纳百川的体现。而在威海路上经营三丰元清真美食家餐厅的马兰花女士1997年来到上海,从三张桌子的牛肉面馆开始做起,最后在延平路上开了自己第一家新疆餐厅也有二十多年了,威海路的这家餐厅也经营了十八年,而她在昆山为苹果手机做配件的工厂里面还有两间给工人就餐的牛肉面馆,也经营了六七年。在浙江中路的经营玛丽亚新疆菜主题餐厅的克力木先生,他们的餐厅在1992年开业至今也有三十多年了。
按照小钊的说法,一个传统的夏季新疆快餐就是一碗黄面加上几串烤肉。黄面的做法类似兰州拉面,因为这种凉面在做面的时候,需要加入了一种生长在新疆山野中的植物蓬蓬草制成的蓬灰。蓬灰这样的强碱性物质,使得拉面格外有韧劲,做面的时候除了面粉、盐和蓬灰之外,再加水搅拌起来就会把面的颜色变成了黄色。有意思的是在上海的很多新疆餐厅并不都提供这个在新疆非常受欢迎的凉面,除了口感之外,可能也是因为做起来比较耗时。
但是小钊还告诉我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新疆人在点羊肉串的时候都说烤肉,而新疆之外的食客都还会把它称为羊肉串。而克力木先生说他们餐厅为了适应本地客人的需求,他们也慢慢习惯把烤肉叫成了羊肉串了。而当我问起马兰花女士清真餐厅和新疆餐厅的区别在哪里的时候,她告诉我清真餐厅在申请营业执照的时候,是需要向工商管理部门特别加注食物要求的,而清真餐厅供应食物的供应商也需要有专门的认定,在羊肉、牛肉、鸡肉以及乳类食品和食用油的供应商需要具有同样的认证许可。另外在传统的清真餐厅是不售卖酒类饮品的,可能有些餐厅会供应啤酒,但是绝对不会供应烈酒。这让我想起之前迪拜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全球著名的喜力啤酒要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建立一个专门的啤酒园区,以供来自全球的球迷共聚一堂。
跟这些新疆的朋友以及热爱新疆美食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传统与改良的此消彼长。无论是菜式的创新,还是主张食材优先的经营理念,都还是在遵循市场规律下而进行的。就好像在上海的日式餐厅一样,真正日本人爱去的餐厅,都不太有机会开出分店,而开了很多分店的日式餐厅,日本人也往往不太会去。
其实这就是每个不同菜系在繁华大都市里面都会遇到的相同问题。如同在上海的新疆餐厅可以吃到的番茄烧牛腩,这样的菜式在新疆当地的餐厅就几乎看不到。而克力木先生最喜欢吃的薄皮包子,也因为担心市场的接受程度而很少在上海的新疆餐厅里面出现。毕竟这种用羊肉以及少量的牛肉还有羊尾油以及少量的青椒做成的薄皮包子,一定要趁热吃。如果在包子冷却之后,馅汁就有可能流出,然后口感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一笼薄皮包子做出来不能马上送到客人的餐桌上的话,恐怕就失去了应有的口感。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食物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也许就是存在改良以及本地化的过程吧!
对于羊肉而言,似乎上海的消费者对于羊肉的膻味始终是一个心理障碍。记得有一次看到蔡澜先生的访谈,他说如果羊肉不膻那就不是羊肉了。这种好胃口的确令人钦佩。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食客而言,气味的确是影响食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真正的烤肉,很多的新疆餐厅甚至连孜然和辣椒面都不放,就放一些盐作为调味已经是非常好吃了。敢于这样做的餐厅,都是源于自家采购的羊肉非常有信心。
有意思的是,不少新疆菜餐厅也会在餐厅的入口处摆放新鲜的羊肉售卖,它们有的是来自于新疆,有的是来自于甘肃,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喜欢热气羊肉,而很少售卖冰鲜的羊肉。那些从大西北空运来的羊肉,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到了虹桥机场之后,餐厅就会去派人去接货,然后放在自己的冷库里面。
每家餐厅卖的最好的菜式,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招牌菜,感觉这是多年以来消费者教育的结果,羊肉串、手抓饭、烤羊排、烤包子、大盘鸡以及手抓羊肉和拉条子。有趣的是大盘鸡的出现则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新疆的餐厅根据川菜辣子鸡的做法,结合了土豆烧牛肉的方法进行了改良。可见一道广受欢迎的菜式,也是在不断的文化融合中发展出来的。我想起以前大部分的川菜都是不辣的,发展到今天全国人民的不辣不欢,也是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
在这些朋友的眼中,耶里夏丽餐厅是上海的新疆餐厅的成功代表。对大部分的上海当地消费者而言,新疆餐厅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的符号:人们在新疆餐厅里面载歌载舞以及吃烧烤。想起那个著名的笑话,少数民族吃饭的时候都会载歌载舞,就是我们喜欢吃饭的时候互相吹牛皮。
不过谈起民族差异性的时候,倒是有一个之前我自己都不了解的情况,就是新疆餐厅里面不会出现青蛙、鳝鱼或者泥鳅这样的食材,似乎他们觉得这些食材不应该进入人类的食物链。想到之前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在餐厅里吃蝉蛹以及水蟑螂,觉得真是一个都不能放过。其实这些昆虫做成菜肴的味道,大概率都是用各种调料浸泡之后的味道,我的一个朋友说这么一点肉甚至还不如大闸蟹的一条腿的肉多。总之人们又回到了“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思考当中了。
对这些正常经营都超过二十年以上的新疆餐厅而言,浙江中路这样的地段,玛丽亚餐厅周末以往都可以做到每天接近十万元左右的营业额,而现在的周末也只能达到五六万元。而马兰花女士在昆山电子厂的两间员工餐厅,原来每个月大概有也有八九十万元的业绩,现在则是变成了每个月五十多万元。宜山路的维吾尔餐厅门口的烧烤生意也只有以往的六成左右。虽然营业额的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另外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更多的消费者都会把新疆餐厅当做一个餐饮消费的日常选择,而不仅仅是当做一个民族特色餐厅。
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样写道:“乌伦古河从东往西流,横亘阿尔泰山南麓广阔的戈壁荒漠,沿途拖拽出漫漫荒野中最浓烈的一抹绿痕。大地上所有的耕地都紧紧傍依在这条河的两岸,所有道路也紧贴河岸蔓延,所有村庄更是一步都不敢远离。如铁屑紧紧吸附于磁石,如寒夜中的人们傍依唯一的火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忙碌,当我问到他们是否看过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的时候,得到的回答都是听说了这部剧的热播,但是都还没有时间去追剧。追剧的人们都已经开始安排暑假的新疆之旅了,但是在上海辛勤工作的新疆餐厅的经营者们依旧还在餐厅里面忙碌着。
有的时候我会想到用“美食之城”这样的名词来形容上海。当然,香港也是美食之城,新加坡、伦敦或者纽约也是美食之城。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食之城?仅仅是因为有很多高级餐厅吗,还是因为有很多个性化或者多样化的餐厅?
米其林美食指南以及黑珍珠榜单或许不能够完全真实地捕捉到上海城市的多样性。而所谓的多样性,也许就是每一条街道的拐角处都有一间社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小餐厅,它们跟周围的居民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它们已经成为了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而这些餐厅的经营并没有被那些所谓的潮流餐厅所带来的那种时髦所改变,而是依旧作为社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那种城市新人以及年轻人或者附近居民都可以负担得起的消费,也许他们的餐厅装修一点都不时髦,甚至都还有些保守或者落后。但如果说上海是一座美食之城,那么就应该可以在一条普通的街道上看到各种不同风味餐厅。如此众多的新疆餐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都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中扮演着一种纽带的角色,或者是一种对西部风情的想象与向往,或者是一种对家乡的思念与期待。总之被食物唤起的力量,让这些普通的餐厅更加真实而温暖。
文章编辑: stdp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