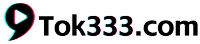责任编辑: zhijiantang.com
上海没有什么好酒,不管是白酒还是黄酒、啤酒,没有一种酒是能拿得上台面的。可上海的糟味确是出了名的嗲。一到入夏,很多老字号餐厅就会推出糟味系列,在外卖窗口上贴上醒目的广告。糟味上市,上海的夏天才正式开始。
入夏前,江南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梅雨季,阴雨连绵,每天落落停停,整个城市像一颗巨大的松茸,那慢慢生长。上海人把这段日子称为“上海第五季”。不过今年上海的黄梅季,没有丁点缠绵的影子,“暴力梅”攒足了力道,狠狠地持续了半个月,让人彻底没了脾气。暴雨、闷热,人身上整体粘嗒嗒的,像是被包裹在密封袋里。
读书时生物课有个实验,是有关植物蒸腾作用的,需要在绿叶上套上透明塑料袋,半小时左右就能看到塑料袋的内壁上会出现液滴,将时间和变化记录下来,实验就算完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共情下植物的感受,相信它们一定是痛苦的。不能正常呼吸,被笼罩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憋闷、用湿热交换湿热,得到的是双倍的憋闷。在黄梅季,整个江南都处在这样的体感里,至于那些雨巷里的丁香,雨巷里的浪漫,都只留在故纸堆里。那个时候,弄堂里走出的不论是谁,顶多能看清阳伞的颜色,至于眉眼都模糊在水气里,氤氲着。
梅雨天里,氤氲着的不光是姑娘的眉眼,还有阳台上的衣衫、书柜里的收藏、以及自己的情绪。望着窗外的雨滴、雨丝、雨帘,无休无止,没有尽头。要说人心什么时候最齐整,那一定是这个时候,全上海的居民都在盼望着出梅的日子,日盼夜盼,哪怕知道出梅后将是连续的高温,那也是好的。宁愿热得融化,也总比困在蒸笼里好,人总是会期盼结局的,不管是好是坏,总要给个说法。一段感情,一场官司都需要一个说法,哪怕是一部电视剧,大结局的收视率总是高涨的。拖泥带水不是这个城市的气质,上海人精明也爽气,不愿意将精力消耗在这么无效的事情上。等待,是留给值得等待的事情,绝不是内耗。
今天的生活已经有太多的不确定,经济、职位,年轻人考学求职,总是在尝试和等待,这些“不确定性”不断地消磨着人心,再也不想经受多一分的折磨。让人奔溃的不是明天上班前的那场暴雨,而是不知道这随身要带伞的日子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当人被困在某种状态中一筹莫展的时候,绝望也就随之而来。
入梅、出梅,气象意义上的指标,成了上海人普天同庆的日子。人们需要这种明确的指标,有了它就好安排自己的生活,该洗的洗,该晒的晒,遇见高温那就防护。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里,这样的生活才是安心的,不管是好还是坏,这个夏天不再需要太多的变数,惊喜和惊吓有时候就在毫厘之间,而生活脆弱地就真得再也承受不了那最后的一次变数。
果然,经过持续暴雨、大火收汁,上海终于出梅了。紧接着就是小暑、入伏和大暑。梅雨和上蒸下煮的日子无缝衔接,高温曝晒如期而至。人们面对这一切,反倒坦然了。该来的它终于回来,和之前的那么多个夏天一样,上海人开启自己的消暑模式。
一年之中有两段日子,上海人最遵循古法,一是春节,二就是三伏天。在人的情感和身体最脆弱和最敏感的时候,一定会想念最舒适的方式。高歌前进的时候愿意尝试各种新奇,当身心慢下来的时候,那些记忆就自然而然得涌现出来。上海的夏天,气温最极端,口味最诚实。什么City不City,那些是属于游客的,上海夏天的日常,就是从那一碟子糟味开始的。
糟,在上海,是名词也是动词,还是形容词。糟,是酒糟的简称,酿酒后的残存品,原本可以扔掉的东西,却在江南人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带着酒的香醇味道,但又不浓烈,不用担心酒量不好,贪嘴耽误事。这种爱,又爱地不彻底的感觉,最适合这个城市。不用赴汤蹈火,也不用死心塌地,浅尝辄止就好,这样还能意犹未尽,期待着下一次,一期一会,每会都能心生欢喜。所以,对于这种度数、分寸的拿捏感,从行为模式,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连口味也受到影响。
酒糟做菜,是取它的味道,滤出汁水,用它来浸泡各种食材。在上海人的手中,万物皆可糟,素的糟毛豆、糟花生、糟素鸡、糟百叶;荤的有鸡、鸭、猪脚、猪耳、猪舌头,上海人管它叫门腔。喜好咬文嚼字的人觉着这种写法不妥,应该是“门枪”才对。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就有回目是“有女长舌利如枪”,说的是峨嵋派的丁敏君当众揭露纪晓芙的隐私,是个长舌妇。《诗经》里也有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所以把长舌比成长枪是妥帖,有据可考的。不过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事情,糟门腔三字一出,食客立即明白是什么,那种糟香四溢、软硬适中的口感会自然而然地萌生出来,若是换成“枪”字,那种硬邦邦,横冲直撞的感觉,肯定不对。上海有位当红的脱口秀演员,就叫“门腔”,人气旺,噱头足,还没邀请去参演《繁花》的舞台剧,一口上海闲话,搭得刚刚好。
很多本地的老字号都会在这个时候,推出糟货系列,一个个不锈钢餐盘整齐地摆放在外卖窗口,和熏鱼、酱鸭、八宝辣酱们一起,它们成就了上海人家最家常的餐桌。虽然如今有成品糟卤出售,在家做糟货也十分方便,但很多上海人还是迷恋老味道。
盛夏的淮海路,梧桐茂盛,它们映衬着一旁的洋房,那些art deco的线条和装饰,被树叶遮掩着,依稀露出容颜,有些斑驳,但依然是美的。街上的大部分商铺都要到10点钟才开始营业,但那些老字号食铺早早开门迎客。老字号大多有外卖柜台,它总要比餐厅早营业,7点多钟的样子,玻璃柜面里就有师傅在那里做准备工作。
说来也有意思,外卖档口的师傅大多体型微胖,脸上挂着笑,带着厨师帽,身上的白色工作服总是很干净整洁。虽说上海本帮菜浓油赤酱,可那些酱鸭熏鱼的酱汁从来不会弄到身上,颇有种武林高手万竹片叶不沾身的侠气。师傅在那整理档口,搬运菜品,玻璃窗外的队伍没一会就排起长队,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阿姨爷叔,一早来采购,安排好自家的餐桌。天气炎热不想进厨房煎炒烹炸,买些熟食,配点小菜,就能吃得很落胃。
若是有客人上门,也会来添菜,热菜和汤自家烧,冷菜大多会买些回去装盘。老字号的熟食,味道熟悉,价格熟悉,连档口的那几张笑面孔也是熟悉的。有的老客人甚至能算出每个师傅的班次,若是轮到他上班的那天换人了,阿姨爷叔多会问上两句“伊啥情况?”,听到只是临时调休才安心,下次遇到了会关心几句“没啥事情哇!”。这一问一答间,人情冷暖和着糟货的香气,一起被打包着,带回老客人的屋里厢。
上海人对味觉是有执念的,但这份执念是有地域界限的,他们不会为了一份糟带鱼奔波大半个城,在他们心里家门口的熟食店就是最好的。带着餐盒走出弄堂,一刻钟的步行就是极限了。上海的市政建设、商业布局向来是围着住宅区而设置的。人们羡慕的那些梧桐风貌区,在解放前大多是租界区,以家为原点,步行半径内有面包房、咖啡馆,甚至是公园,这种社区布局方式成为了上海的核心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淮海路上有两家餐饮老字号,一家老人和,一家光明邨,两家只隔一个路口,转身就能到。老人和饭店历史悠久,是真正有据可查的百年老店,它最早创建于1800,上海开埠前就已经存在。最早店面开在城隍庙老城厢附近,叫“人和馆”,那句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店名的来历。这段历史在《光绪上海县续志》中有记载。后来因为一段店名侵权官司,干脆改成了“老人和”,几经辗转,店铺搬到了今天的淮海路中心地段。老人和的糟货是上海滩有名的,是堂吃的招牌菜,尤其是那道糟鸡更是拿得出手,据说想当年连大亨黄金荣都欢喜。那年头的大佬们口味大多念旧,他们欢喜的就是那一口正宗的味道。
相隔一个路口的光明邨,解放初期曾经是一家点心店,到了1990年才改建成“光明邨大酒家”。能不能准确地念出酒家的名字,可以作为对上海熟悉程度的判断标准,而能不能说出“邨”字的来龙去脉,那基本可以作为上海历史专家的认证标准。
“邨”是个异体字,读音和含义和“村”一样,但有意思的是,上海那些老实公寓太多用“邨”,比如“陕南邨“,原名是亚尔培公寓,又名皇家花园公寓。是1930年法国人投资建造的,红砖外墙有白色线条装饰的几何图案,楼内的水磨石地面上有马赛克的拼接花纹,小小的一块块整齐地镶嵌在楼梯台阶上。这里曾经居住着大明星王丹凤、翻译家周克希,虽然如今这里回归平静,但那些拉毛外墙和黑色铁窗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底色。
同音的那个“村”,也用来为住宅区命名,大多是解放后建设的新村。比如曹阳新村,建于1951年,是解放后全中国兴建的第一个人民新村,是当时的陈毅市长命名的,择址也是老市长拍板决定的,当时很多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都搬去安家落户。新村是另一种风貌的体现,它们都是上海,但又如此不同。不过上海始终是包容的,它可以海纳百川,不同的发展时期给这个城市留存下不同的印记,存在即合理,“邨”和“村”各自安好,和谐共存。
保留着“邨”字的光明邨大酒家门口常年排着两条长龙,一条是买鲜肉月饼的,这里的鲜肉月饼一年四季都有,但一年四季都要排队。另一条队伍是熟食档口,酱鸭、熏鱼、八宝辣酱,传统的本帮风味这里都能拿得出手。《繁花》电视剧里宝总犒劳爷叔,也会到光明邨多买几个小菜摆在台面上,字幕组也是老老实实用了“邨”字,和酱鸭一样原汁原味。
入夏后,熟食档品添了糟货,一如既往的品种,一如既往的味道,一如既往的老客人。阿姨爷叔们穿得山青水绿的,一早出来排队。早上天气风凉些,菜品也新鲜,有些卖得好的品种,稍晚一些就卖光了,那多可惜。一日三餐是头等大事,安排好这些,再去喝咖啡会朋友,老人家的生活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主次分明。
餐桌上糟香四溢,清爽可口,这是这个城最地道的上海味道。也许还有栀子花、白兰花,以及装在绿色玻璃瓶中的花露水,但那种香气时常留存在记忆里,伴随着电风扇的嗡嗡声响,它们一起营造着怀旧的气氛,让人总是惦记着儿时的美好。那时候还有暑假,那时候的暑假还是纯粹的开心的。
可回忆总是片面的,洒满花露水的傍晚依然酷热,弄堂里的暑气久久不能褪去。一天下来栀子花、白兰花也开始发黄,香气越来越淡,要想再换一朵,得等到第二天的清晨,那又将是一个高温天。唯有这餐桌上糟味,这么多年一直没变,把多年的记忆一起包裹浸润。
十年前上海本帮菜申遗成功,《舌尖上的中国》里的那道扣三丝,成了上海菜的代表。那家三林塘的铺子整天挤满食客,吃道扣三丝得提前好久预约。扣三丝,那是冬日席面菜,卖相好,费手工,还带着“金山银山堆成山”的好口彩。若是哪天糟货也单独申遗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把上海的夏天一起打包。
若是离开了热浪滚滚的街道,亲疏得体的弄堂,还有那一声叠一声的上海闲话,那糟味也就不再那么迷人有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间,是糟味,更是夏天的这个城。
文章编辑: zhijiantang.com